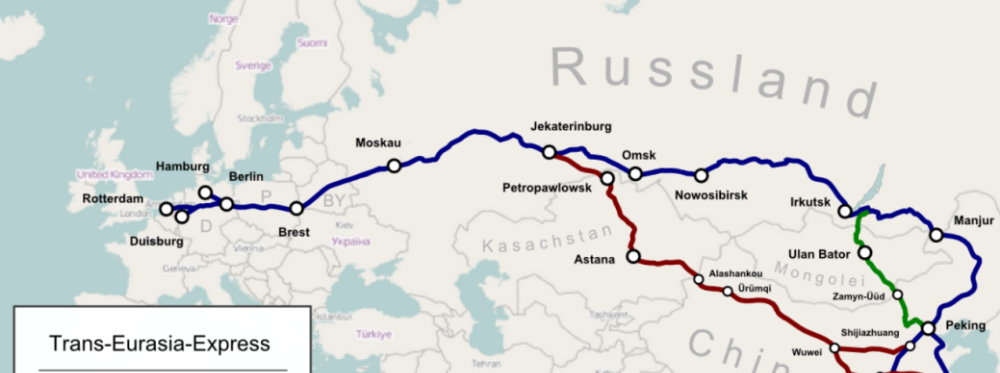赞
赞
城乡的贫富差异,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以前有读者给我留言,让我写篇文章,说说教员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正好我也比较感兴趣,那就写篇文章和大家聊聊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篇文章的内容,我只罗列和教员相关的史料、讲话、文章,不涉及任何个人分析,所以篇幅不会很长,点到为止,希望大家能理解。近现代的城乡关系,总体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前,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的社会生态是城市富农村穷、城市为主农村为辅、东部城乡碾压西部城乡。在这种社会生态下,上海的十里洋场和陕甘宁的偏僻农村,几乎是天上地下的两个世界。于是,教员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因为在农业经济时期,农村虽然穷,但农村有土地、粮食、人口、兵员以及各类物资,属于社会生态上游的生产单位。城市虽然富,但一切生活物资都需要从农村采购,所以城市是社会生态下游的消费单位。革命的重心下沉到农村,相当于釜底抽薪。一旦教员把农村整合起来,城市便失去粮食、物资、劳动力的供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和大海中的孤岛似的,随时会被四万万人民形成的磅礴伟力冲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说起来千头万绪,核心逻辑,其实就这么几句话。革命重心从农村到城市,有一个转移的过程。早在1944年8月,教员给博古的信中就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949年3月,教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两件事,标志着……

 赞
赞
 赞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