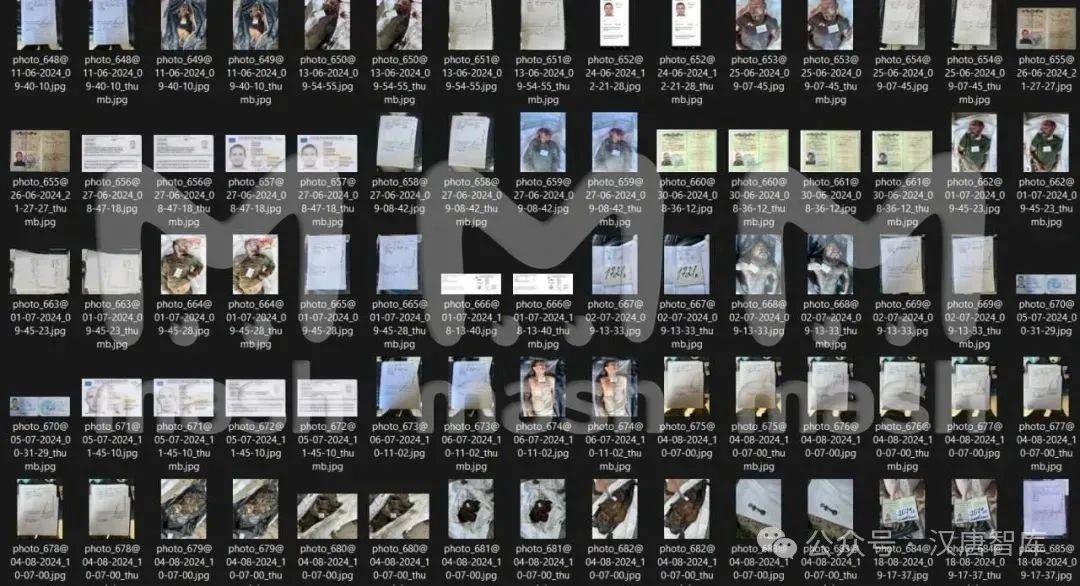赞
赞
01
据《广西日报》消息,6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柳州市债务化解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了
自治区支持柳州市本级一揽子化债方案
柳州市本级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实施方案
会议强调,柳州的债务问题,看似金融风险,实则是政治生态问题。
……
02
柳州的债务问题有多严重?
我简单搜了搜不同口径的统计数据,感觉差异还挺大的(以下数据仅为参考,我不为其真实性跟准确性负责)
截至2024年末,柳州政府显性债务余额为1042.72亿元,其中一般债务271.03亿元,专项债务771.69亿元。
1042亿是什么概念呢?2024年柳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950.67亿元,其中柳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49.09亿元。
1042亿和149亿虽然看起来差别很大,但是其实这个负债率还算正常。许多地方的债务和收入比,比这个要高不少,
但是更关键的是隐形债务,有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24年末,柳州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规模达2397亿元,远超显性债务,隐性债务主要集中于城投平台(如柳州投控、东城集团等),占广西全区城投债余额的40%。
这两千多亿可能还只是有息债务,其他的诸如工程款呀,政府承诺的奖补资金,拖欠的工资费用等,可能还不知道有多少。
假设这2397亿的“有息负债”利息是6%,那么一年的利息留就要143亿。换句话说,柳州全市所有财政收入,不吃不喝,可能归还隐性债务的利息还不够……
这才是制约柳州发展的最大制约。
03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影响呢?从“柳州市债务化解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专题会的表述,可以窥见一二:
首先是政绩冲动裹挟下的决策失控。
柳州债务危机的直接推手,是前两任主政者郑俊康、吴炜主导的“大跃进式”城市扩张战略。2016年,柳州提出“一主三新”城市发展蓝图,将轨道交通、产业新城等作为核心抓手,试图通过基建投资拉动GDP高速增长。
然而,这种决策完全脱离实际——例如轻轨项目在未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的情况下强行上马,总投资额高达186亿元,却因人口密度不足、运营亏损风险过高等硬伤沦为“空中楼阁”。最终形成176.95亿元隐性债务窟窿。
其次是权力监督失效下的融资狂欢。
郑俊康、吴炜主政时期,权力寻租与金融杠杆深度捆绑:一方面,城投平台成为政商利益输送的管道,直接导致项目成本虚高、质量失控;另一方面,自治区分管领导蓝天立、唐仁健等人默许甚至纵容违规融资,形成“上级背书+下级操作”的共谋链条。
更致命的是,债务扩张与个人升迁直接挂钩——主政者通过“负债换GDP”创造短期政绩,而接任者因忌惮风险暴露选择“借新还旧”,最终形成两千多亿元债务雪球。
最后是产业转型滞后下的经济失血。
柳州债务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困境。作为“西南工业脊梁”,柳州长期依赖汽车、机械等重工业。但是,2024年,其燃油车产量同比下滑,柳钢集团也净利润暴跌,这都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现况。
2024年柳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9亿元,同比下滑4.8%,而债务利息支出高达143亿元,形成“财政养债”的恶性循环。更严峻的是,土地财政依赖症加剧失衡——2018年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收比重达45%,但随着楼市降温,2024年该比例骤降至18%,进一步削弱偿债能力。
04
那柳州的债务问题是个例么?当然也不是。本质上柳州今天的困局,也是一个时代的尾声。
柳州债务危机绝非孤例,而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债务驱动增长”模式的缩影。
这座工业重镇的困局,折射出地方政府在政绩冲动与债务扩张之间的深层矛盾——当“负债换GDP”的短期逻辑取代了高质量发展的长远考量,当权力寻租与金融杠杆形成共谋链条,系统性风险便如影随形。
而今天彻底暴露的危机,也揭示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终结: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扩张、倚重基建投资的增长引擎、依托政商捆绑的融资狂欢,在人口红利消退与产业转型压力下已难以为继。
那未来应该如何办呢?或许这次“柳州市债务化解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专题会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答案:
柳州市和各县(区)、市直部门“一把手”要扛稳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推动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不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不搞短期行为和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不给后续发展留下烂摊子,在发展历程中跑好自己这一棒,以实干实绩实效推动柳州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赞
赞
 赞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