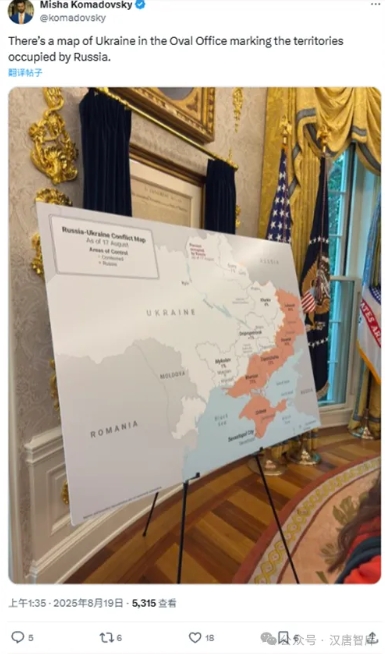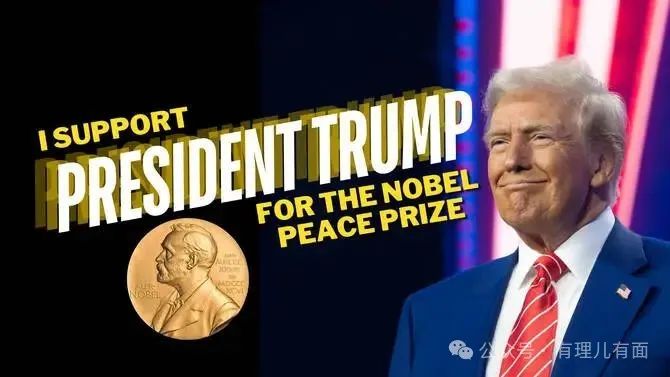赞
赞
01
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王朝引以自豪耗费巨资兴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泱泱中华帝国却败给了“蕞尔岛夷”的日本。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两,还给予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等特权,失败之惨亘古未有,条约之苛刻令人发指,这给一向妄自尊大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同时二百兆白银的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常年国库收入的三倍,为了支付这批赔款,清政府被迫举借外债,财政压力空前提升。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要说1895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应该一蹶不振才对。不过,现实,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02
1895—1913年,十八年的时间,全国新设资本1万元以上的工厂468家,总投资额9822万元,远超战前水平。
作为对比1872-1894,二十二年,全国有资本可查的商办厂矿只有为53家,资本额为470.4万元。
主要以轻工业为主,纺织(如大生纱厂、申新纺织)、面粉(福新公司)、卷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发展迅速;重工业初步萌芽,如汉冶萍公司(钢铁)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比如张謇与大生集团,1896年白手起家,就以棉纺织为核心,延伸至垦牧、航运、教育等领域,形成综合性资本集团。
1915年,大生纱厂的产品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南通也成为近代工业模范城市。
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企业不但没有被彻底摧毁,反而愈加茁壮起来。
这是因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国人从沉睡中惊醒,不甘沉沦的民族自尊心使各阶层的人们,为了民族自存不得不重新审视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封建体制和社会现实。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之后始也。
同时因为,《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在华设厂,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并应对民间呼声,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1896年下令各省设立商务局,鼓励绅商投资实业,从法律上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入侵进一步瓦解了自然经济(新质生产力摧毁久产业体系)但同时外国在华设厂客观上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本土企业通过模仿逐步提升竞争力。
同时,通商口岸的开放扩大了商品市场(开放全球市场)。
03
甲午战败的屈辱并未扼杀民族生机,反而激发出“实业救国”的浪潮。
在政策松动、资本积累和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民族企业以轻工业为突破口,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这一看似矛盾的繁荣背后,实则深刻揭示了国家发展的真相。真正扼住发展咽喉的,从来不是列强的炮舰与赔款的重压,而是内部落后的产业结构和盘踞其上的既得利益群体。
甲午之前,真正限制中国方发展的瓶颈,是根植于旧产业结构与食利阶层的顽固抵抗。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官办军工体系,虽耗费巨资却形同虚设。
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装备依赖外购、维修仰人鼻息,正是重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跛足的血泪写照。战后虽出现汉冶萍公司等重工企业,却依然难逃官僚资本的低效窠臼与外资钳制。
与此同时既得利益集团更是以有形无形之手阻碍新生力量的崛起。传统地主士绅视工商为“末业”,保守官僚则担忧新式企业动摇其权力根基。
旧势力为维护特权,宁愿选择抱残守缺,甚至不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利益藩篱,比《马关条约》的锁链更加窒息民族生机。
04
所以,当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舞面对外部危机,并不一定是“灭顶之灾”。
因为往往最深刻的改革策略,只有在最大危机倒逼下,才能真正出台。
决定一个民族存续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外部风暴的猛烈程度,而在于内部结构能否在风暴中实现艰难的重塑。
真正致命的枷锁,始终是盘踞于旧有经济基础之上、抗拒变革的顽固利益集团及其所维护的低效结构与落后思维。
 赞
赞
 赞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