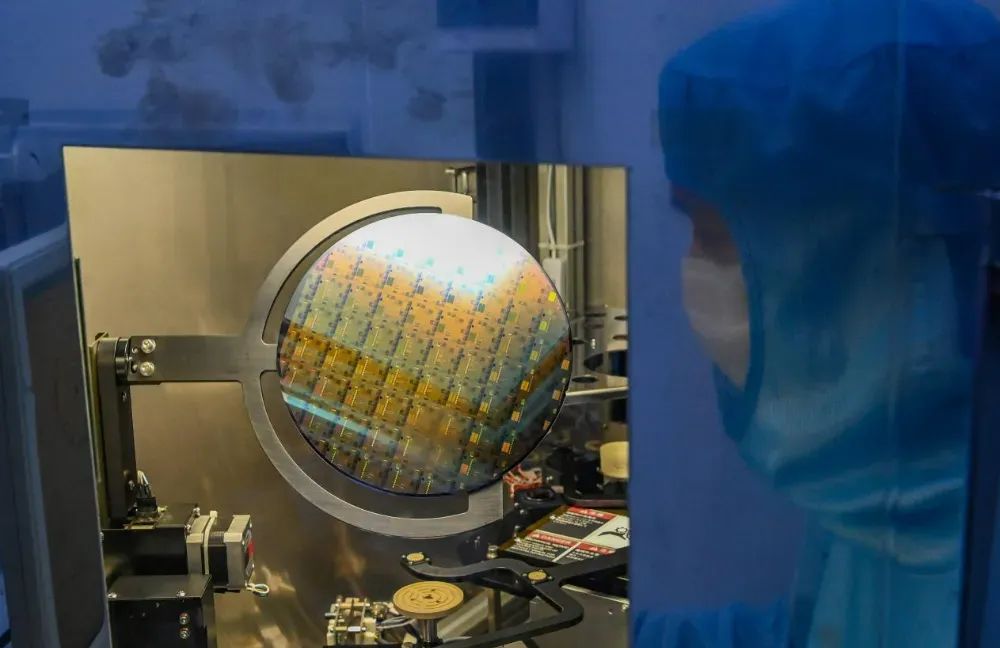赞
赞
泡泡玛特的“情绪容器”

每个人都是情绪价值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这两周泡泡的热度下来了,可以来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关于“情绪消费”这件事。
为什么会有情绪消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情绪价值的生产者,也都是情绪价值的消费者。
我在2017年开始研究情绪消费,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开头从一个经典问题开始:“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
社会家的答案是,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你还付出了“情绪劳动”。
大部分直接面对客户的职业都需要付出“情绪劳动”,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
扩大了说,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礼”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
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在后面要加一句,也没有白干的活。所有标准服务规范的职业,工资实际上都包含了“情绪劳动”的回报,对情绪的要求越高,回报也理应越高,所以空姐的收入比火车服务员高,星级宾馆服务员收入比一般旅馆高。
职场也是如此,同样的工作能力和贡献,擅于情绪劳动的员工(比如会揣摩上司心态、拍马屁)比“低情绪价值”员工收入高,这多出的一部分,就是付给情绪劳动的,这样,人才能达到“情绪平衡”。
但是,员工工资只与企业效益有关,在经济好的时候,情绪劳动的报酬容易满足,经济不好的时候,你需要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回报却可能更少,为了达到“情绪平衡”,这个“欠额”,就需要花钱“买”情绪价值。
这就是情绪消费的需求来源,它有一定的反周期性,经济不好时,情绪消费的需求量反而上升,就是经济学中的“口红经济”。
情绪消费是现代社会的必需消费,以媒体为例,提供的情绪价值和信息服务的价值同等重要,比如《新闻联播》,对于非公职人员,其提供的信息量已经非常微弱了,主要作用就是传播“正能量”的情绪价值。
如果说十几年前的传统媒体,情绪价值与信息价值还是三七开,现在更受欢迎的自媒体,就完全倒过来,粉丝越多的号,情绪价值含量越大,信息只是一个包装,甚至是假的也无所谓,只要每天来几个“赢麻了”充电情绪价值,明天继续牛马倍儿有劲。
扯远了,虽然很多商品本身都包含情绪价值,但能够把情绪价值直接商品化,甚至拥有知识产权的,就只有潮玩盲盒这个赛道。
情绪容器
泡泡玛特刚刚上市时,投资者最困惑的事(其实现在也是),没有任何影视角色,凭空设计几个IP,价值到底何在?
其实与影视类IP相比,非影视IP商品中包含了很多的情绪价值,更类似于情绪价值的容器,而非情绪价值的本身。
根据荣格的“原型理论”,人类对某些具象但留白的形象天然有共鸣,因为它们可以承载不同的“心理原型”。
泡泡玛特的IP形象都有空白表情、模糊性别、超现实风格,容易让人投射自己的情绪,赋予想象。例如Molly的冷漠脸、Labubu的怪诞气质,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个性表达。
影视角色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哈姆雷特是极具复杂性的角色:忧郁、聪明、犹豫、愤怒、疯癫……,这种多面性可以让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读出自己”:
有人觉得他是理性而深思的王子,可能是因为读者向往这种气质
有人认为他是懦弱犹豫的悲剧者,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也是童年受害者
有人看到他对父亲的忠诚,可能这是他非常重视的价值观
有人关注他对母亲的愤怒与焦灼,可能这种情绪也曾困扰过他

所以,同一个角色,不同的阅读者能从自身经验出发,投射出不同的理解。
心理学中称之为“投射效应(Projection Effect)”,即,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性格、经验、情绪,投射到所观察的人或事物上,从而得出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
但“复仇王子”这个角色的内容被确定后,一千个人心中的哈姆雷特,只是有少许不同,读者的心理投射是受限制的。
之前,有IP运营商把《柯南》中的经典影视IP乱磕CP,引发了粉丝的强烈不满,正是因为过于具象的画面,侵犯了读者的“心理投射”,而原剧刻意模糊,正是为了给读者留下自我解读空间。
而一千个人眼中,就真的有一千个Labubu,这个没有任何内容的形象,好像只是一个容器的形状,消费者可以自由地安放自己的各种心情,完全是消费者的内心投射:
一个压力山大的白领,看到的是一只咧嘴假笑内心倔强的自己
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看到的是一只没人理解却活得自在的怪物
一个情感受挫的人,看到的是一只外表强硬、内心脆弱的小动物
一个社恐症患者,看到的是一只不说话但依然活得精彩的家伙
……
先有人设与审美,再用设计感触发消费者的多巴胺奖励,引发收集的兴趣,这种由艺术家和粉丝共创出的意义,而非剧情驱动,是一个纯粹的闭环,至于隐藏款、二次创作,都是营销手段,并非商品的本质。
一个IP,就可以为我们无处安放的情绪,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容器”。
很多人都说无法理解这种塑胶小人有什么好买,这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个,人人都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一刻,需要这样的“情绪容器”。
这个东西反正也不贵,你去挑几个你看得顺眼的,放在书桌前,有空的时候就看一眼,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你在看它的时候,内心忽然产生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情绪,而从此刻起,这个IP就为你的这种情绪,赋予了特定的形状,产生了永久的连接。
IP爆款的偶然与必然
说完了“情绪容器”,第三个话题是IP爆款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Labubu早在2017年就首次登场,是泡泡玛特IP序列中的“长尾”,核心圈是少数原漫画角色的粉丝,少有“路转粉”,2017-2019这三年,Labubu的小怪物系列都是一个小透明。
主要是因为,很多人第一眼看到Labubu的感受就是“好丑”,不像Molly那样符合主流的“可爱美学”。
但“审丑消费”其实一直存在,像Crocs洞洞鞋、马面裙,都是“先丑后香”,各种丑萌表情包,更是代表“审丑”情绪的广大空间。
可爱和丑的心理投射机制不同,前者是“好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后者是“我就是这样的,丑,但是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后者往往代表“有个性”“不媚俗”,成为年轻人世代用来反抗“老登文化”的符号。
另外,相比“可爱”的形象,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软化”那扎眼的特征,才能作为“情绪容器”被接纳,往往具有“延迟爆红”的特点。
到了2020年,随着大众审美的多元化、在Molly、Dimoo等“软萌型”IP主导市场多年后,一部分消费者产生了疲劳,转而追求更有棱角、性格化、反差感强的角色,对“怪可爱”的接受度提升,Labubu就恰好契合了这种心理转变。一些小众玩家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晒娃”,到了2021年,Labubu慢慢变成一种审美态度的标签,慢慢渗透进更多盲盒玩家的视野,部分隐藏款价格开始上涨。
不过,正常情况下,国内的审美氛围对这一类形象的包容度的极限就是“盲盒玩家”,就像暗黑系的“SkullPanda”商业价值很难超过Molly,Labubu真正向外破圈,实际上走的是“出口转内销”的路径。
Labubu率先于2023年在泰国走红,原因正是泰国年轻人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度在全球范围来说都算是很高的,泰国Z世代和Y世代中,高比例未婚,支出多用于悦己与情绪消费,对鬼怪恐怖片、LGBT文化、搞怪短剧、宗教混搭、文化拼贴的接受度非常高,Labubu的形象在国内是“小众丑萌”的另类文化,但在泰国反而刚好是主流,泰国本土爆红的角色如 MaewMaww(鬼猫)、各种怪兽类手办、搞怪佛牌贴纸,都是此类形象,所以才会被泰国公主这种公众人物接纳。

到了2024年Labubu在全球多元文化氛围比较浓的国家和地区爆红,再“出口转内销”,强行让国内的主流媒体关注,多少有点“被教育”的味道,因此,Labubu的出圈,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特例,但也大大打开了未来泡泡玛特IP类型的空间。
从Labubu的这种“厚积薄发”中可以看出,人是会成长的,“情绪”并非一成不变,情绪容器想要保持其商业价值,就需要不断在主流与小众中寻找平衡,当旧的小众成为新的主流,就需要寻找更新的小众IP,这就是一个沙里淘金的游戏,只有足够多的IP,才能创造出新的爆款IP,是一个天生有利于龙头的赛道。
另外,IP潮玩可以跨越语言隔阂,这是天然优势,Labubu主要是暗黑童话与哥特风的结合,基本上没有东方元素,却可以在多个文化圈流动,等于把市场规模扩展到全球,让一款IP得到多个文化圈的淘金机会,提高了胜率。
IP的生产和运营才是泡泡商业逻辑的核心,而盲盒这一种形式,只是“拉新”的工具。
情绪价值类商品的商业模式
除了潮玩外,很多商品都有情绪价值。
化妆品消费除了功能性的需求外,还提供一种可视化的自我认同,是一种面向内在而非他人的“悦己仪式”。你用的不只是粉底、口红或香水,而是在安慰内心的焦虑,表达此时的心情,建立面对世界的安全感,犒赏辛苦的自己,给明天一个更好的开始。
“变美了”和“觉得自己变美了”,都很重要,但却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分别代表了化妆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不同美妆品牌,功能可能差不多,但提供的情绪价值却有天壤之别。
除了潮玩和化妆品外,提供情绪价值比较多的商品还包括:
服饰搭配类:特别是搭配类,泡泡玛特在推出毛绒挂件后,突破了潮玩的品类限制,从自我疗愈到社交符号,拓展了情绪容器的功能
咖啡茶饮:放松、独处时光、沉浸感,可以看看今年微醺的传播形象“晚9点,微醺中”,满满的情绪价值
游戏数码影视:逃离现实、掌控感、成就感
旅游:重启生活、逃离现实、现场感
沐浴洗护类:解压、切换、舒缓、爱自己
家饰香薰灯光:归属感、安心感、自主权、生活美学
宠物:陪伴、依赖、情绪投射、爱与被爱
从这些定义中你会发现,上述大部分商品(除游戏、旅游和宠物)都有很强的功能性,情绪价值只是附着其上,消费者只会为功能性买单,如果品牌过度强调情绪价值,反而有“智商税”的嫌疑,如果品牌不能把功能和情绪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割裂感。比如咖啡茶饮,消费者对情绪价值的溢价能力接受有限。
还有一些商品,比如服装的功能性和情绪价值往往是矛盾的,情绪价值高的款式,往往“穿不出去”。
所以这些商品,情绪价值只是提供产品的附加值,不能成为商业模式的核心。
剩下的游戏、旅游和宠物经济,功能价值与情绪价值都是合一的,这一点跟盲盒潮玩相似,但它们从商业模式上说,都各有各的问题。
游戏影视是被动参与的内容产品,能容纳消费者主动创造的情绪的空间有限,消费需求上更侧重于内容而非情绪价值,这一点与实体商品消费没有区别,而内容制作的商业模式很差,以前的文章分析过。
旅游消费的也是情绪价值,但大多数公司是“不可复制地理价值+难以标准化服务”,没有规模效应,空间有限。
其中唯有宠物,与非影视IP类盲盒潮玩在情绪价值上是最相似的,都是情绪投射的最佳情绪容器,宠物本来就是个会动的大玩具。但宠物经济卖的不是宠物本身,只是周边产品,都是实体商品,也存在功能性与情绪价值的分割,而潮玩拥有对IP的专属权,破解了“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商品模式上更好。
当然,潮玩也并非完美的商业模式,它高度依赖头部IP,经营有极强的偶然性和一定的周期性。
 赞
赞
 赞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