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赞
赞
9月15日,上海多所学校爆出午餐中的虾仁炒蛋被发现有臭味而紧急撤换时,绿捷说:“虾肠外溢,有泥沙”。
9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市监局、教育委三部门联合通报,因学生餐中虾仁被下架一事,绿捷公司涉嫌瞒报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并控制相关人员。
9月23日晚,这家日供50万份午餐、掌控上海近三成校园配餐市场的巨头,发布了一则“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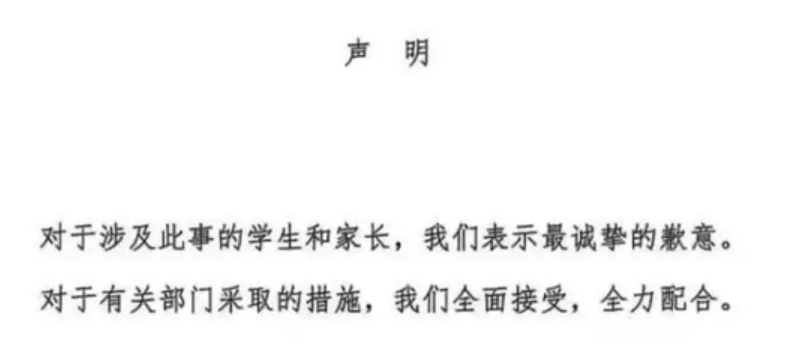
“这份声明”发布与上三部门联合通报是同一天。
一边是政府部门的严肃执法,一边是企业的轻描淡写,变味的不仅仅是虾仁。
对于像绿捷这样的企业而言,校园是一个规模庞大、需求刚性、现金流稳定的“优质客户群”。
校园餐市场不同于普通餐饮市场,其特殊性在于“封闭性”与“强制性”。一旦成为供应商,合同往往锁定三到五年,中途更换极难。
家长的抱怨、学生的吃不饱,都成了可以“内部消化”的噪音。
首先,沟通与反馈机制的低效甚至缺失。
家长个体的投诉,往往需要经过班主任、学校后勤部门、学校领导等多重关卡,才可能传递到供应商那里。
在这个过程中,抱怨和投诉很容易被“消化”或“过滤”。
学校也可能出于维稳、避免麻烦或与供应商存在利益关联的考虑,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终,家长的呼声被消解于无形。
其次,“替代选项”的匮乏。
绝大多数学校明令禁止学生自带午餐,理由五花八门:食品安全难以保障(指学生自带的)、管理不便、影响集体秩序等。
凭什么不让孩子自己带饭,买个保温饭盒,早上烧好装好放书包里就行,我初中就这么带的。
所谓“自己带饭不安全”的底层逻辑,实在经不起推敲。
自己给自己下毒?
做饭把自己毒死,还是给自家孩子做饭?
所谓“安全”,在某些场景下,已成为一个方便拿来使用的“万能借口”,用于限制选择、规避责任。
这种规定,实质上剥夺了家长“用脚投票”的最后权利,将孩子们牢牢地锁定在单一的供餐体系内,别无选择。
再者,集体行动的高成本与高风险。
个别家长的激烈抗争,可能会被视作“麻烦制造者”,甚至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到无形的影响。
组织集体维权,则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社交成本,且结果难料。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大多数家长最终只能选择妥协,将担忧埋在心里,转而叮嘱孩子“不好吃就少吃点”,或者额外准备一些零食。
这种妥协就成了在权衡利弊后的一种现实选择。
万万没想到,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孩子们过的如此艰辛。
说实话,监狱里的犯人也不可能给吃发臭的饭啊。
对下一代健康福祉的保障标准,难道不应该高于对触犯法律者的基本生存保障吗?
这种对比,让一切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而破局之路,在于透明,选择与问责。
 赞
赞
 赞
赞





